从广济禅师到三平祖师——由《唐广济大师行录碑》说起
- 财经
- 2025-04-09 12:23:03
- 5
本文原刊于《中国宗教》杂志2025年第3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苏轼题《唐广济大师行录碑》跋文
缘起:宋代碑文里的历史掌故

三平祖师塑像
中国古代素有刻石立碑以铭史的传统。近年,作为苏轼文章和书法传世的新发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题跋《唐广济大师行录碑》拓本一经面世,便引起广泛关注。此碑刻立于宋代,该拓本是明嘉靖墨拓本,有历代递藏者的题跋、笺注、收藏印等,弥足珍贵。
据《四库全书》史部十四《金石文考略》载:“苏文忠广济大师行录小楷书《唐广济大师行录碑》,王沨撰。沨与禅师同时,苏文忠书并跋。其字圆劲不必言,妙在运笔天然, 若不知作小楷者,故为小楷中所难也。”可见此碑的书法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和宗教研究价值都极高。
《唐广济大师行录碑》碑文内容由唐代王沨(即王讽,唐吏部侍郎,谪守漳浦,乾符中入为工部尚书)撰写,记载着唐代广济禅师的生平事迹。二百多年后,苏轼在宋代重修的碑文上跋文,讲述了广济禅师的教诲与修行精神。
广济禅师俗姓杨,名义中,祖籍陕西高陵,因父仕闽,唐建中二年(781)出生于福唐县(今福清市)。从小不食荤腥,少年时随父宦居泉州。14岁时,随父仕官至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投宋州律师玄用出家,27岁时受具足戒。他精通经史,尤其擅长《周易》,先修习奢摩他(止)和三摩钵提(等持),后来修习禅那(静虑,即住心一境以静息 念虑和思维真理)。为求证佛法,云游参学、遍访高僧,先依百岩怀晖禅师,历奉西堂智藏禅师、洪州百丈怀海禅师、抚州石巩禅师,再侍潮州大颠禅师,并成为大颠的法嗣弟子。
禅师于唐宝历初(约825年)回福建弘法,至漳州,入平和、漳浦,最后在漳浦与平和交界的三平山上“因芟剃住持,敞为招提”。当时他的弘法吸引学众云集,“学人不远荒服请法者,常有三百余人”。唐会昌五年(845),因武宗毁佛,避居平和九层岩山,在大柏山麓建成三平寺继续弘法,并传授百姓桑麻耕织技术,带领民众垦创田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大中三年(849),唐宣宗即位后,重新尊崇佛教。漳州刺史郑薰特请禅师出任漳州开元寺住持,并将其事迹上疏朝廷,宣宗敕封为“广济禅师”。咸通十三年(872)十一月六日,广济禅师宴坐示寂,世寿92,僧腊65。
此文书写的年代初步断定是宋神宗元丰年间,落款“东坡居士轼跋”。约是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所著。“东坡”是当时黄州东门外一块山间坡地,苏轼在此处养牛一头,垦田半顷,播植稻麦,自号东坡居士。受佛家思想的熏染,苏轼心情发生巨大改变,在《黄州安国寺记》中反观自己过去言行皆不中道,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苏轼是在何种渊源之下书跋《唐广济大师行录碑》,还有待深入挖掘和考证。但在字里行间,苏轼表达了自己对广济禅师的景仰:“余独爱其载师最后语云:‘吾生若泡,泡还如水,三十二相皆为假伪。汝等有不假伪底法身,量等太虚,无生灭去来之相。’呜呼!大师,吾得而见之矣!曹溪法门,惟论见性,斯非其一语印南宗者与?”读罢广济禅师的法语,苏轼发出感叹,表示自己有幸仿佛亲眼见到了大师!
苏轼对禅宗有着深刻的理解。禅宗南宗要义即是强调人人本具先天佛性,只要真智显露,就能明心见性、内外彻悟、见性成佛。在他看来,广济禅师印证了南宗曹溪法门要旨。他还在跋文中摘录广济禅师的偈子:“只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呈君”,发出体用不二之慨。该偈末两句云:“个中若了全无事,体用何妨分不分?”——广济禅师“全无事”这一心无所住、无有所得的禅悟,与苏轼的人生意趣是极为契合的。
广济禅师的禅法同样影响了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唐广济大师行录碑》言及广济禅师“复引韩愈侍郎,通入信门”。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舍利,上书《谏迎佛骨表》,被贬潮州任刺史。虽是被贬谪,但韩愈上任后因俗施教、移风化俗,结果潮州大治。元祐七年(1092)苏东坡撰写《潮州韩文公庙碑》,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碑文中高度赞扬了韩愈的文学成就以及任职潮州的政绩。而后两句“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颇有东坡自况之意。可惜《潮州韩文公庙碑》的真迹已不能得见,而《唐广济大师行录碑》碑帖存世更显珍稀至极。
据《祖堂集》记载,韩愈曾到大颠禅师处参问治理潮州事宜,禅师良久未答。侍者广济禅师在背后敲禅床,大颠乃云:“作摩?”对曰:“先以定动,然后智拔。”广济禅师以禅言慧语替大颠禅师解答了如何治理好潮州的良方妙策。韩愈豁然开朗,对广济禅师钦佩不已,云:“和尚格调高峻,弟子罔措,今于侍者边却有入处。”在潮州期间,原本辟佛的韩愈通过与大颠禅师、广济禅师的往来,对佛教有了新的认识,这也成为儒释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广为流传。
演变:从禅师到祖师的发展脉络

16 世纪日本室町时代,狩野元信绘《祖师图》(局部),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此幅画为当时流行的屏风画,共四扇,描绘了中国禅宗的多个公案故事,其中之一是《三平受箭、石巩张弓》。
广济禅师所处的时代,正是禅宗流派纷呈的时代,南宗由洪州、青原向五家七宗过渡。他四处参学各宗派高僧,博采兼容,对禅法有着深刻的领悟。《五灯会元》记载着著名的禅宗公案“三平受箭、石巩张弓”。广济禅师拜学于石巩禅师时,石巩以弓箭接机,他毫不犹豫擘胸以对。石巩30年间以弓箭接引学徒,只有广济禅师略明其旨,得到了他的首肯,他称自己终获“半个圣人”。后来广济禅师再悟得石巩张弓、直指本原的机锋,说:“登时将谓得便宜,如今看却输便宜。”自唐末以后,禅宗五家七宗有将近百位禅师在禅悟教学、开示和教化中都用过这则公案。在诸多禅宗典籍里,都有关于广济禅师问禅悟道的记录,可见他是一位师承南宗,对达摩禅法有着透彻理解的高僧。
宋以后至明清时期,广济禅师由一位禅宗高僧演变成被广大民众崇奉的“三平祖师公”,三平祖师信仰逐渐形成。
诸多碑文记载了广济禅师精于神通法术的传说故事。宋大观四年(1110),三平寺第一次重修寺内碑刻时,当时的住持僧云岳在所附的修碑题识中提到广济禅师“鬼窟活计”的传说:“世之比拟广济大师鬼窟活计,乃谓小乘。如斯言议,涉在常情。俗谚井谈,道听途说。”在修碑时,云岳将其时已广为流传的禅宗典籍中所记载的广济禅师的语录,以及民间有关其传说补缀于碑。
《唐广济大师行录碑》以及寺内现存的明清碑碣中,加入了不少关于广济禅师的民间神话传说,相比于唐代最早关于广济禅师的史料内容有了较大的变化。这些故事还见载于当时所撰修的一些志书,如嘉靖《龙溪县志》、明代何乔远《闽书》等等。这些传说故事结合闽南地理环境以及民间动物崇拜、神灵崇拜的背景,把三平祖师塑造成一位佛法无边、本领高强、能够驱妖降魔的地方保护神。
类似这种由高僧大德转变为神明祖师的例子在闽地还有不少,例如闽东平麓祖师、闽南清水祖师、闽西定光古佛和伏虎禅师、闽北三佛祖师、闽中卢公祖师等。
三平祖师自唐宋以来就被当地民众广为崇仰。从寺内碑刻记载来看,其信众以漳州地区民众为主,上至漳籍朝官,下至地方文武官员、乡绅士庶以及黎民百姓。著名者有宋吏部尚书颜师鲁、颜颐仲祖孙二人,明万历年间礼部侍郎林釬,明崇祯年间吏部主事陈天定,清乾隆《四库全书》正总裁、文华殿大学士蔡新,清康熙“一等海澄公”黄梧及其曾孙黄仕简等。他们或捐修三平寺,或增置寺田,对三平祖师信仰的深化和传播,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平寺迄今香火绵延不绝,每年都会举办内容丰富的信俗活动。2014年,“三平祖师信俗”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传播:交流交往的桥梁纽带

漳州平和三平寺
三平祖师信仰作为佛教与闽地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其信仰体系、文化内涵等经过不断丰富与演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俗文化。三平祖师信仰形成之后,主要流行于漳州地区,后来逐渐向周边地区辐射,扩散到整个闽南地区。据碑刻资料显示,早在元代就有温陵(泉州古称)人助三平寺修碑,乾隆年间又有“泉厦分府蒋元福等人”参与捐修三平寺。
明清时期,随着一些闽南人逐步迁移至台港澳及东南亚等地,三平祖师信仰也随之播迁。在台港澳及海外,有诸多三平祖师庙、三平宫、三平院、三平广济宫等庙宇,都是在三平寺祖庭庙名基础之上的演化。三平祖师文化包含的“广济、和谐、发展”“慈善大爱、济人利物”等理念,植根于中华文化,深受海内外信众的认同与尊崇。
闽台一衣带水、渊源深厚,三平祖师信仰也在明清时期随先民迁徙传播到台湾,并发展绵延至今。据统计,台湾有三平祖师分庙50多座,信众数十万人,分庙常常举行盛大的三平祖师信俗活动。两岸三平祖师信仰同根同源,多年来,常有台湾信众前往三平寺祖庙朝圣,并组织进香团到三平寺进香,祭拜三平祖师并恭取香火回台湾,络绎不绝。当前,三平寺以及三平祖师信仰已成为对台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在联系台胞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从广济禅师到三平祖师,这一信仰传承生生不息。作为闽台文化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深入研究阐释三平祖师信仰及其内涵,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进一步凝聚人心、增进两岸情谊具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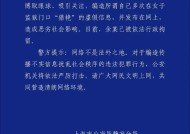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