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拉美:可乐、汉堡与一个更大的世界
- 财经
- 2025-04-08 16:38:04
- 5
可口可乐成功地超越了其创始人们最大胆的梦想,它作为一种年轻的、充满活力的现代性标志,早已被老生常谈地提升到了作为美国帝国主义象征的地位。1880年,可口可乐在约翰·彭伯顿(John Pemberton)的亚特兰大药店的后屋中诞生。在这里,他在一个铜制的大桶里用木柴生火煮出了一种由草药、种子、糖、咖啡因和古柯叶组成的奇怪混合物。这种混合物最初是用来治疗头痛、抑郁和宿醉的药物,当不小心与苏打水混合后,它就从药用饮料变成了一种能令人愉悦的饮料。但遗憾的是,这种饮料只吸引了几百个顾客。彭伯顿把它卖给了更有远见的企业家阿萨·坎德勒(Asa Candler)。

约翰·彭伯顿
坎德勒接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聘用了彭伯顿的前会计(负责标签的书法字迹的人),然后在1892年创立了可口可乐公司。 10年后,近80家装瓶厂相继投产,到1904年,超过350万升的浓缩配方饮料销往全国各地。Takola Ring、Coca Conga、Coca Gola、Coca Kola等异名产品的竞争一夜之间冒了出来。坎德勒担心口渴的普通顾客可能会随意选择这些听起来名字相似的饮料中的任何一种,这促使他的一个合伙人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诀窍是设计一种一眼就能认出来的瓶子,甚至是蒙着眼睛都能识别出来的。1913年,公司设置奖赏以征集最佳设计,很快,一名在官方历史上被称为“某爱德华兹”(a Certain Edwards)的无名学生设计出了可能是地球上最广为人知的图标。他在《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中搜索古柯植物(其叶子是可乐配方的一部分)时,无意中看到了一幅类似榴弹凸出纹理的可可树豆荚草图,而作为巧克力来源的可可树与可乐毫无关系。他从鼓胀的豆荚模型开始,在石膏模型上塑造了一个底座,拉长了瓶颈,并在侧面画了垂直的槽线,让人联想到一个穿着飘逸衣服的女人。事实上,这个曲线型的瓶子更像是那个时代穿着窄底裙的、身材丰满的吉布森女孩(Gibson Girl)。红白相间的字样取自美国国旗。一年后的1914年,可口可乐公司最初发行的100美元的单股股票价值上涨到了1700美元。1919年,坎德勒的继承人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他们持有的股票,当时是北美工业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
在美国禁酒时期(1920—1933年),可口可乐在公司最大股东罗伯特·伍德鲁夫(Robert Woodruff)的领导下蓬勃发展。伍德鲁夫被称为“可乐先生”,是公司的官方“英雄”,他所倡导的一个关键特征一直没有被抛弃。无论是在日本旅行的美国人,还是在墨西哥旅行的意大利人,都不会注意到可乐的味道或表现形式有丝毫不同。不管用什么地方的水,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可乐浓缩液都必须是一样的。伍德鲁夫很有智慧地看到,花体的字样和吉布森女孩样式的瓶子都会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他在1929年提出的广告语“享受清凉一刻”(The Pause That Refreshes)至今仍在我们身边使用,现在有了80种语言的版本。
1941年,面对战时限制国内消费的可能性,伍德鲁夫制定了两个策略。他设法将可乐转化为爱国主义的标志,把可乐瓶放在“战争的前线而不是后方”,随时准备鼓舞军队的士气。战争中的男女无论在哪里,都应该能以5美分的价格买到可乐。他宣称,这种饮料会唤起士兵心中对遥远祖国的记忆,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女友或母亲在同一时刻也可能在享用可乐。这是个绝妙的举动,该公司成功地将在遥远前线作战的部队与国内的团结一致联系在一起。通过可乐,海外的士兵和国内的家人通过同一种“圣餐”联结在了一起。公司设计了特殊的搬运设备,使可乐瓶可以不受破损地在坦克、飞机、吉普车和卡车上运输。1943年6月,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向位于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总部发出紧急请求,要求向北非前线运送300万瓶可乐。一年后,公司打破了之前所有的销售记录;到1948年,公司每年在广告上的花费达到2000万美元,这对其他任何行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伍德鲁夫的第二个策略,是在欧洲仍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进军拉丁美洲市场。
1926年,可口可乐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开设了装瓶厂,次年又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设厂,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可口可乐才开始大举渗透拉美市场。1942年,公司在阿根廷设立了首批装瓶厂,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到20世纪70年代初,布宜诺斯艾利斯超越纽约成为可口可乐在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城市市场。在战后的年月里,美国软饮料公司在拉美进行了大量投资,广告力量全面转向了数以百万计的潜在消费者。巨大的可乐“瓶子”在斗牛场上舞动,数以百万计的灯光招牌、雨伞、记分板、空白的墙壁、餐巾纸——任何“可能被一双以上的眼睛同时看到”的东西都印有可口可乐的商标。
拉丁美洲的市场迅速扩大。当可口可乐在当地遇到竞争时(比如在巴西广受欢迎的瓜拉纳[Guaraná]饮料或者是更晚出现的地区性的图百依那饮料[tubaínas],事实上,瓜拉纳早在1942年可口可乐到来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公司降低了产品的价格,或者为当地的装瓶商提供了一整套难以竞争的营销方案,尤其是可口可乐公司能够花费80万美元来确定用一只充满母性的母袋鼠作为最可能吸引女性消费者的广告手段,女性群体贡献了该公司在巴西80%的销售额。1993年,可口可乐公司占有巴西60%的市场份额,百事公司占有13%的市场份额,这使得当地其他生产商不得不争夺剩下的份额。在秘鲁,印加可乐(Inka Kola)从1935年被发明以来,就作为替代进口软饮料的民族主义产品得以推广。许多秘鲁人将印加可乐视为民族自豪感的象征以及该国丰富美食的完美补充。到1995年,这家秘鲁公司还能跟上可口可乐的步伐,基本上分享了每年约7500万加仑软饮料(每人约50罐或瓶)的相对较小的市场。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可口可乐公司收购了这家秘鲁公司50%的股份。
墨西哥人是拉丁美洲最热衷于软饮料的消费者,事实上,他们的人均消费量和总消费量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美国居民。虽然面临着来自当地生产商与百事可乐等企业的一些竞争,但可口可乐公司仅1998年就在此售出了16亿箱。这相当于墨西哥男人、女人和儿童每年的人均消费量约为426瓶,即每天消费一瓶以上的可乐。20年前,墨西哥的软饮料年消费量约为每人250瓶。由于墨西哥放宽管制,取消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前对外国软饮料征收的40%的税,百事可乐和可乐都向该国倾注了数十亿美元,后来又开始收购当地的软饮料公司。可口可乐在墨西哥软饮料市场的占有率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40%上升到了如今的65%。
尽管瓜拉纳、印加可乐、巴里托斯(Barrilitos)和其他水果口味的本地软饮料在当地被宣传为更健康的、民族主义的可乐替代品(即便可口可乐巩固了它作为美国帝国主义最重要象征的地位),但越来越多的拉美人依然选择且正在选择彭伯顿先生发明的令人愉快的混合物。可口可乐的吸引力渗透了社会各个阶层,该公司的广告以儿童和穷人为目标,这种做法被一位营养专家称为“商业性营养不良”。

1943年可口可乐广告
回到本书开篇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获得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为什么拉丁美洲人喝那么多可口可乐?第一个答案可能是,它比水更安全;另一个答案是,它相当便宜。对中产阶级来说可能是这样,但对普通人而言,一罐12盎司的可乐可能要花掉近一个小时的工资,比瓶装水贵得多。其他的人可能只是喜欢这种味道,或者觉得瓶装饮料方便。但可口可乐不仅仅是一种软饮料。它的广告一直将可口可乐与现代性和“美好生活”联系在一起,包括摇滚乐队。大力度的营销将软饮料融入到新的家庭仪式中,而这些仪式本身也是由广告创造出来的。当完成一项任务或是一家人聚在一起时,那就是时候“享受清凉一刻”了。求爱、跳舞、摇滚音乐会和体育赛事等都离不开可乐。最后,它本身的外来性也是一种资产。可乐整齐地包装着放在冰柜里,用壮观的专用卡车运载,这些都印载着熟悉的标志,代表着现代的、都市的、世界的——这些词曾经是“文明的”同义词。
虽然有些人认为可乐是傲慢的帝国主义的另一种肤浅表现,但对更多的人来说,也许只是在潜意识中,可乐让其饮用者与更大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就像18世纪墨西哥的混血泥瓦匠在掰开一块小麦面包时的感觉一样,
也许也与一个“美好年代”时期里约热内卢的花花公子在穿上一套新的英国花呢西装时的感觉一样。在这三种情况下,消费部分衍生于权力——不是来自总督的法令,也不是来自遥远的英国萨维尔街(Savile row)的优雅模特,而是来自广告所创造的直接、持续的形象。为什么是可口可乐而不是百事可乐?为什么有了可口可乐,“一切都变好了”?也许是因为老彭伯顿的会计用他的专业书法画出了令人难忘的原始标志,或者是因为“某爱德华兹”在丰满的吉布森女孩身上看到了他独特的瓶子设计的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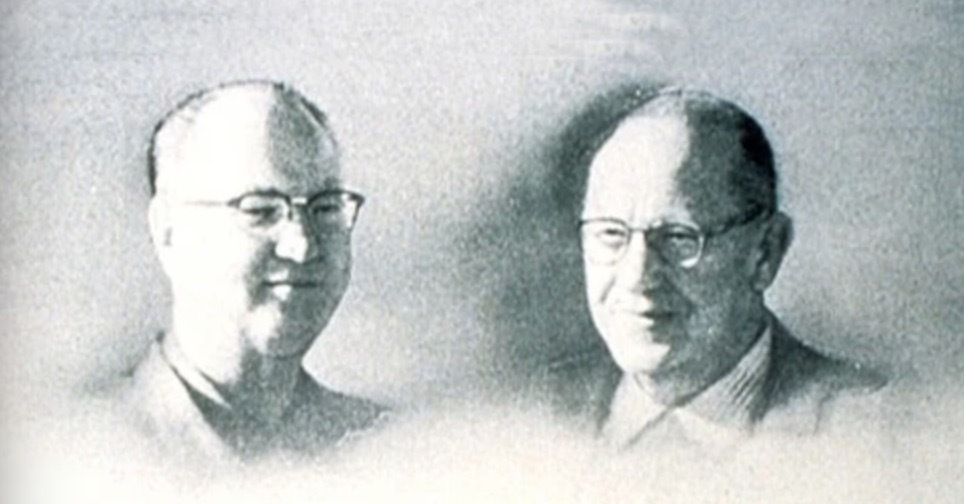
理查德·麦当劳和莫里斯·麦当劳(Richard and Maurice McDonald)兄弟
麦当劳在世界范围内的起步比可口可乐晚,但现在金色拱门的标识遍布各地,引领着整个拉丁美洲快餐店的爆炸性增长。1937年,理查德·麦当劳和莫里斯·麦当劳(Richard and Maurice McDonald)兄弟在加州帕萨迪纳市开了一家小型汽车餐厅。在成功的激励下,他们在洛杉矶以东50英里(约80公里)处的一个蓬勃发展的工人阶级小镇上购置了另一个更大 的地方。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福特式的汉堡包流水线制作方式,他们每年的收入达到了35万美元。这引起了以向食品工业销售电子搅拌设备为生的雷·克罗克(Ray Kroc)的注意。其他人曾提议将他们的方法推广到其他餐馆,但麦当劳兄弟缺乏雄心壮志,他们说“我们现在赚的钱都没办法花掉”。克罗克先生则更有说服力。理查德和莫里斯加入了他的团队,然后同意以很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名称、特许经营商的命名权与他们的制作系统本身。到1961年,巨无霸汉堡在全国250家带有金色拱门标识的餐厅里煎炸制作,麦当劳兄弟被踢下了船。
为了保证产品的统一性,克罗克建立了自己的“大学”,专门培训管理人员和工人,有竞争对手将其与海军陆战队相提并论。到1987年,也就是克罗克去世的三年后,麦当劳连锁店已拥有9900家分店,公司销售额达到143亿美元。当时,麦当劳的9900家餐厅还贡献了可口可乐全球销量的5%。那一年,仅在美国,消费者每天吃掉的绞碎牛肉就达500吨,如今这一数字已达到了两倍多。1987年,公司已经在广告上花费了6亿美元,仅电视广告就投入了3.25亿美元。这比通用汽车公司多出了5000万美元,也是其业务内容最类似的竞争对手汉堡王的两倍。像其他快餐和垃圾食品的供应商一样,麦当劳的广告也以孩子为目标。他们的代理公司创造了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丑“麦当劳叔叔”,他会表演滑冰、骑自行车、游泳和打球等。“麦当劳叔叔”是孩子们的好朋友。这些策略得到了回报。在20世纪80年代末,麦当劳获得了42%的7岁以下顾客,比快餐业整体数据高出10%。
麦当劳第一次进军海外是在1970年,当时快餐在国外市场还相对不为人所知,尽管在美国已经很普遍了。即使如此,该公司还是不得不调整其菜单以适应当地人的口味。一开始,生意清淡;打入加拿大市场需要降价20%,而且最初6年根本没有利润。但此后,生意有了起色。到1987年,海外有2000多家麦当劳分店,贡献了全部销售额的20%。
这家公司进入阿根廷的时间较晚,阿根廷的大部分中产阶级甚至部分工人阶级早已习惯于每月几次外出就餐。但到了1985年,当麦当劳第一次植入其金色拱门和当地版本的快乐小丑时,收入分配模式呈现出人们熟悉的、现代的、不平等的形态。对餐馆食品的需求萎缩,并呈现两极分化。“高档”餐厅迎合了新精英阶层,而大量以前能够“坐下来用桌布和餐巾,吃两道不同的菜,外加一瓶酒、甜点和咖啡”的人,发现自己如今只能偶尔吃巨无霸汉堡和炸薯条了。
然而,阿根廷是个例外,该国的工人阶级能买得起麦当劳或其他快餐。到目前为止,快餐是较富裕阶层的零食。在进入阿根廷的同年,麦当劳也来到了墨西哥,但当地只有“穿着考究”的顾客才会排队品尝第一批四分之一磅汉堡(Quarter Pounders)。车辆在麦当劳汽车餐厅的窗口前堵得水泄不通。该店宣称开业第一天就卖出了10000个汉堡包。在巴西也是如此,麦当劳的销售市场还没有广泛渗入城市中产阶级以下的阶层,但即便如此,巴西的人口超过1.8亿,而且大部分城市人口集中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麦当劳公司在这里取得了其在拉美地区最大的成功。从1979年在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建立第一家分店开始,麦当劳在20年的时间里将巴西打造成其在全球的第七大市场,设置了近千家餐厅和摊位。1997年底,该公司宣布将再投资10亿美元,将拉美地区的分店数量增加一倍,以抵消美国市场销售放缓的影响。跨国食品公司的影响在拉美人口中迅速扩散,虽然这部分人口规模相对较小,但仍在不断增长,这些人驾驶汽车、去商场消费购物。跨国食品公司还提供各种各样的美味食品,如水果圈(Fruit Loops)、多力多滋(Doritos)薯片、可可脆饼(Cocoa Krispies)、莱芙士薯片(Ruffles)和玉米芝士片(Pizzarolas)等。例如,百事公司(Pepsico)
是墨西哥最大的咸味零食和饼干加工企业。我们可以自信地预测,进入21世纪后,金色拱门、巨大的塑料小丑、闪烁的巨型热狗标志和吸引人的肯德基上校将把美国先进的饮食制度更广泛地传播到拉丁美洲热切的消费者中间。

2011年4月21日,位于巴西圣保罗的麦当劳餐厅。
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往往会排挤本地的生产商,转而提供统一的工业化产品,但墨西哥手工业生产的增长却为标准化提供了一个显著的对比。尽管墨西哥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强制性的工业化计划并一直持续到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期(1994年至今),但艺术和手工艺仍然蓬勃发展;事实上,手工艺匠人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例如,在1980年左右,大约有600万人(当时总人口的10%)从事艺术和手工艺。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条件下,手工业生产如何在有大量印第安人成分的拉丁美洲国家生存甚至增长?
有一个直接的解释:人口增长以及土地稀缺导致较贫穷的农村居民寻求更多的收入,因此他们转而从事具有深厚传统的工作。他们制作布料、衣服、陶器和许多不同的艺术和手工艺品。墨西哥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国家艺术工艺发展基金(The National Fund for the Promotion of Arts and Crafts,简称 FONART)支持这种努力,将其作为进口替代工业政策的一部分以及推进内部社会统一、国家形成和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目标。国家提供的鼓励措施还旨在减缓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促进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和手工艺非但不是矛盾,实际上还符合资本主义霸权的全局,因为它们有助于提升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的自我再生产能力。
墨西哥的艺术和手工艺品也依赖于大量的墨西哥和外国游客,他们有各自的理由购买手工艺品。在一个商品消费与生产越来越分离的世界里,许多人似乎想“用更简单的生活方式建立象征关系”,寻求与自然和“代表那种失去的亲密性的印第安工匠们”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因此,数以百万计的游客(仅1977年墨西哥米却肯州就有200万游客)摒弃首都城市大型的、便利的国家艺术工艺发展基金大卖场,甚至不去如今美国那种更方便的大型奥特莱斯,而选择直接从乡村的手工艺匠人们那里购买物品。美国密尔沃基(Milwaukee)的客厅里摆放着来自埃龙加里瓜罗(Erongaríguaro)的工艺品,也是在“为出国旅行作证明”(并暗示社会经济地位和闲暇时间),表明一个人有足够的“文化”去接受这些异国商品。此外,在一个越来越统一的世界里,“广告悄悄向我们所有人耳语”,告诉我们所有使自己的生活与他人不同的方法。
但是,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周围充斥着种类繁多的物品,我们怎么能说这是一个“越来越统一的世界”?难道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有众多的“选择”吗?如果想象一下1940年堪萨斯州一个乡镇农场的物品种类和数量或者墨西哥城郊区塔库巴亚一个体面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物质财富,再与如今呈现的物品相比,我们毫无疑问地会惊叹于第一种情况下单调统一的吊带连体服与第二种情况下或多或少相似的“墨西哥现代的”家具。但当时这两个地方都与芝加哥的中产阶级郊区截然不同。而如今,这三个地方的物质文化会有惊人的相似性。可以肯定的是,冰箱、电视机、汽车或T恤衫的品牌(brands)不同,但物品的种类(categories)却近乎相同。地区性和国家性的差异正在消除,被纳入全球模式。
在米却肯州的具体案例中,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与传统手工艺之间的相互关系逻辑推动了消费领域的双重运动。工匠们自己也不太穿手工制作的衣服了,使用的陶罐、木勺和芦苇椅也少了。这些物品正被“因其设计或现代内涵而更便宜或更有吸引力的”制成品所取代。与此同时,由于墨西哥本国城市和国外对不寻常的异国情调的需求,他们自己的手工业生产得到了恢复,甚至蓬勃发展起来。
(本文选摘自《物品、权力与历史:拉丁美洲的物质文化》,[美]阿诺德·鲍尔著,周燕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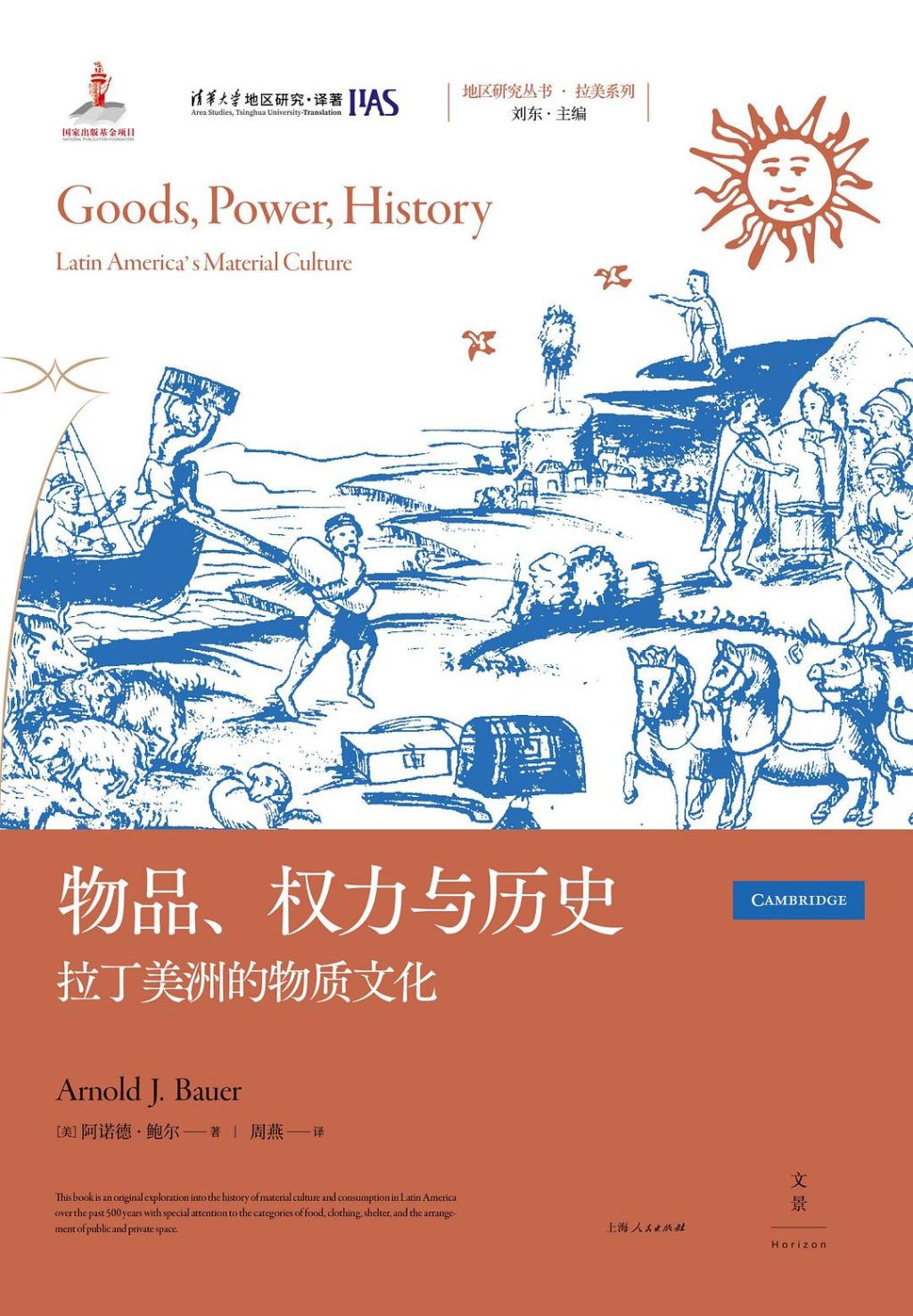
















有话要说...